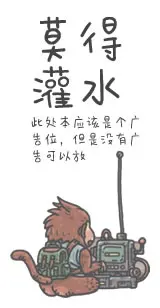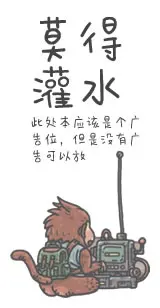這一篇的稿子在幾年前就收到了,但是作者對劇情和文筆方面一直不滿意,就沒有發表。直到幾年后的今天,還是決定從記憶的角落把它翻出來,即便有這樣那樣的不足,也算是一個歸宿吧。
海平線
作者——竹勿言 如果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了,你會做什么呢? 曾經,我也想過這個問題。一個本子上有類似的處境,主角無所事事地蕩去學校,遇上女孩兒。天空染成一片紅色,巨大的隕石下,他們做愛了。
當然,本子里總是要做愛的。可我不免想到自己——年已十八,尚是處男。最后一次天氣預報說,(說來可笑,向來不準的預報唯有這次準得很)隕石將在今天傍晚五點落下。 我下了客廳。母親雙腿交疊,單手持書。父親站在陽臺處,雙手負在身后背對著我。 “我要出去一趟。” 我說。 媽媽抬起頭。 “去哪?” “就是出去走走。” “早點回來。” 我猶豫了一下。 “你不擔心我嗎?” “擔心啊。但擔心能阻止你出去么?” 我搖頭。 “而且,你才十八歲,但你就要死了。會有什么想去做的事吧?” 話語脫口而出。 “如果我想去殺人呢?” “那就去殺。” 我吃驚地說不出話來。 母親又說:“早點回來。” “好。”頓了頓,“我不是去殺人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我當然不是要殺人,我只是想上街,隨便找一個女孩兒做愛。或許到了現在,做愛已失去了它原本的意義。和吸毒、抽煙、打游戲或任何即時享樂的行為沒有任何區別。父母學生時代便拍拖了,然后有了我。他們做愛想必是為了有一個孩子吧。 母親是一名大學老師,父親是一名司機。有了孩子,母親一生便只能被綁在家庭中。年輕時,她的夢想是環游世界,然后在某個歐洲國家開一家咖啡店。如今閑暇時,母親便在家里看書。在我小時候想必更忙,換尿布,哄我睡覺。五歲前,我體弱多病。父親開著他那輛老舊的標志四處載客,無暇管我。母親便從學校請假,帶我去醫院。我覺得是自己奪去了母親在歐洲開咖啡店的未來。有一次,我問她為何要那么早結婚。她說,那時候看父親打籃球很帥,喜歡上了他。長大后就結婚了,沒有想那么多。我問她后不后悔。她回答,到了現在,已經不會再想這些東西了。 現在,我正走在街道上。鐵網被往來的小孩兒圖近路剪開了口子。樹根猙獰地吸住了泥土,瀝青丑陋地向上凸起,裂開;對面的人行道,有兩個人在打架。馬路空蕩蕩。熄了燈的車輛停在路邊,灰塵薄薄一層。我獨自徘徊,沒有行人,更遑論想要找到一位游蕩者,她也恰好是為了想要和某人做愛而踏上路程了。 我掏出打火機,點上一支煙。火苗左飄。這說明風從西邊吹來,往東方而去。 職中退學的那天,我坐在江邊的欄桿上點上十六年以來的第一根。那時,腦海里浮起的是幾年前,爺爺拒絕了化療,奶奶將他接回家,度過人生最后的一段時光。他時常咳嗽,隨身帶一痰盂,從身體深處嘔出帶血的痰。奶奶勸他戒煙,爺爺便在奶奶出去時偷偷點上一根。吸幾口,咳幾聲。吸幾口,咳幾聲。 一個男人站在電線桿前撒尿。男人有些尷尬,但尿還沒結束,它在空中劃過一道半圓,撞到桿子,濺向周遭。
他向我打了個招呼。 “嘿。” 我點了點頭。 他不在意,自顧自往下說:“真不可思議,是么?一個月前我還在手機發布會上演講,一個月后世界就要結束了,大家都得死。” 這時我注意到了,他似乎是小米的老板,雷軍。但我不確定。 他結束了,晃了晃那玩意兒,提上褲子。 “我一直很想這么做。”他解釋,“往電線桿上撒尿。可惜現在街上沒人了,加上你,只有兩個人路過。這也不錯,你懂得,沒人看見就了無生趣。你呢?你想做什么?” “做愛。” “做愛?噢,我懂了。是不少人這么做。而且在這種環境下。那你做了么?” “我還在找。但我一路上就看到你,還有兩個人在打架。” 他有點驚訝。 “找?意思是你還沒約好么?” “是沒有。但既然有十八歲的處男想破處而瞎逛在街上,應該也有十八歲的處女想破處而瞎逛在街上吧,我猜。” “恩……”雷軍沉吟,“本來我想介紹你一個場所,那兒全是做愛的人。可你想要的不是那樣的對吧?” “可以這么說。” “你記得我剛剛說的話么?除了你,大概是五分鐘前,我還看見一個人。那是一個女生,我沒向她搭話。畢竟是女生嘛。她去了那邊。” 雷軍指了指前方。 我向他道謝。 “不用!畢竟那是你的愿望嘛,和我想要在電線桿上撒尿一樣。祝你好運。” 上坡不是很陡,路的兩邊是居民的房屋。一個女人往長線上晾曬衣物。男人坐在門檻上發呆。路邊,遺失的傳單沒了骨頭似地翻滾。遠方,煙囪縷縷冒出黑煙。 我想,即便是下一刻大家都要死了,人類的生活也不會有太多改變。要吃飯,要晾衣服,要撒尿。剛才,我看見一個剛出生沒多久的嬰兒躺在母親的懷里吃奶。比起他來,我或許是幸運了很多。我已活了十八年,就算再活幾十年也不一定會比這十八年更加充實。可是,對于那個嬰兒來說則有些不公平。才出生沒幾天,見識不到世間或美好或丑陋的一切便要就此死去。如果可以,我想問問那位母親,如果早知道這樣,你還會把她生出來嗎?或許她也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。我應當問問那個精子,說:嘿,恭喜你在幾億的同胞廝殺中勝出,成功和卵子結合在一起。可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。兩年后,也就是你剛降世一年多一點,一顆隕石就會砸下來,地表上的所有人類都會死光光,包括你。你怎么想?你還想熬過十月懷胎,然后出生嗎? 我拐過兩道灣,走過一條小巷,繞過小溪,踏過數不清的人行橫道。現在,周圍已荒蕪起來。大馬路寬闊而空曠。路的兩旁栽滿樹木。幾間廢棄的廠房建在樹林里,墻磚剝落,開在頂棚的窗戶爬滿綠色的青苔。很早就偏離方向了。可我并沒有故意尋她。如果她是我要找的那個女孩兒,那她自然會出現。而如果她不是我要找的那個女孩兒,就算找到也沒用。 風咸咸地,且涼。海岸就在前邊不遠了。路面逐漸潮濕,沙子粘在鋪滿路面的石子的縫隙里。爛了的漁網趴著。死魚浮在還有淺淺一點水的水箱里。這兒曾是一個海鮮批發市場,整個鎮上,乃至整個省的人開著汽車,貨車來到這里。它們是幾個月前來這里捕魚的人們留下的。 長長的石墩無限延伸。沙灘在那邊,馬路在這邊。海天一色,細浪撲來又卷去。女孩兒站在淺灘處,海水淹沒了腳踝。
我跨過石墩,走到她身邊。 女孩兒眺望著遠方。 我仔細端詳她。 臉頰微胖,是那種看了令人放松下來的胖。眼睛是藍色的。鼻子普普通通。嘴唇小巧紅潤。我不知道旁人怎么評價,但我認為她很美。 “你在看什么?” 我回答:“看你。”又問,“你在看什么?” “自己看。” 我順著她的視線望去。 夕陽半沉于海平線盡頭,燒云點著了整片天穹,浪尖爍爍閃動。 “怎么樣?” “很美。” 她扭過頭來,我也恰好移開視線。她的藍色瞳孔里是我的瞳孔。 我們異口同聲。 “我是處女。” “我是處男。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