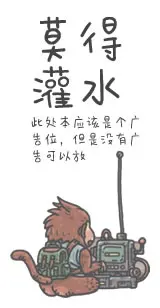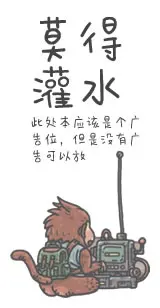|
岡仁波齊
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荒原上,我在糙礪的地面上靜靜坐著抽起煙。
我從南充開始沿318國道的大致線路入藏,騎了三天哈雷,途中只在雅江和芒康停留了兩次稍作休息。我原本來的目的是岡仁波齊,出于莫名的情緒,我忽然想看看它,于是給工廠請了長假,騎上哈雷一路向西。而走318國道到不了岡仁波齊這事,我也是知道的,因為騎到雅江后,我詢問了當地人。
油底殼被磕出個大口子的哈雷倒在一旁,我沒有走鋪裝好路面的國道,那會堵車。而是尋些小轎車難以駕駛的險路或搓板路,一邊享受無人的風景一邊騎行。這也是它拋錨的原因,在去往波密的路上,它下落時磕在了一塊黝黑的巖石上,油灑落一地。
我所處的這片荒原在芒康與然烏湖之間,視線已經可以觸及遠處一角的雪山。
這里的天很奇妙,不同于我生活的福建那樣灰白,是藍色的。它藍得太過純粹,卻又不是油彩那樣厚實的藍,而是透著脆弱的質感,可以凝視很久。我想這有部分是雪山的原因,黝黑的身子骨往上撅起一塊銳利的白,中和了天空的顏色。而另一部分原因是高原的風。凜冽清厲的風吹拂著我的發絲,我的臉龐,還有我瞇起的眼睛,中和了我眼中映出的幻影。
吸罷一支煙,扔在地上踩滅。肺部一陣微微悸動,稍微克服的高原反應借著煙開始反撲。我遙遙望著雪山,我想從下午待在這直待到落日,等天色晚了,我再推著哈雷走上個把小時回芒康,然后修好他,繼續旅行。
現在還沒到擔心晚飯的地步,我還能悠哉游哉。這其實是因為我不知去所,只是沿著這條國道晃晃悠悠地騎行。據說一直走下去能去到稻城亞丁,那兒很美,可我不想去看城,只想去看山。如果我一路騎行找到沒有人發現過的山,它或許就成了我獨有的岡仁波齊。可國道只能去別人去過的地方,見別人見過的風景。我唯獨好奇岡仁波齊為何如此神圣,好奇那些匍匐的磕頭是在朝向誰。
我聽見了豬在哞叫的聲音,身后摩擦沙礫的稀碎的步子聲,我轉頭一看,是個戴著帽子,黑黑的少女,她身后是牦牛群,在荒野上晃蕩著啃著干草。
她很不生怯地盯著我,對我說,你坐在這兒看什么?
我說看那個,指了指遠處冒尖的雪山,她認真地從我的角度瞧了兩眼,也發出贊嘆的聲音
因為車壞了,只能在這里看看。我告訴她,沒抱有能被這個小女孩幫助到的心思。我問,從然烏湖看是不是更好看。
她微笑著說是的,那笑里帶著一絲自豪,我接著問她,你看過岡仁波齊嗎,我聽說那是你們的圣山,很美,而且很神奇。神奇在什么地方,我也沒有了解過,只是聽說而已。
沒想到女孩搖搖頭,表示沒有。
我有點驚訝,你是本地藏民嗎。女孩臉上生出不悅,當然了,我還是編織烏爾朵的冠軍呢。她上身是米白色的麻衣,下身是藏青色的我也不認識的衣物,折起圍在腰間。
她從衣服上抽出灰白色的一條長繩,撿起一塊石頭套在這個長繩頭上,毫不猶疑地抽向一頭伏地不動的牦牛。那聲豬叫原來就是牦牛發出的,我看見她臉上的那分得意。我想這根繩子就是所謂的烏爾朵,女孩小心翼翼地將它掛回腰上。
我騎行在路上時,見過禿鷲啄食牦牛尸體,禿鷲們一埋首,再一抬首,血肉在沙地上一點點漫開。我聽說西zang的自然就是如此,我總覺得眼中的景色無關殘忍與血腥,而是一種野蠻卻深沉的自然。小女孩臉上的得意也是如此。
我望著開始慢慢踱步的牦牛,問她,你真的沒有去看過岡仁波齊嗎?她說是的。而且,她補充說,我當然隨時可以去。
岡仁波齊是藏傳佛教四大神山之一,是中國十大名山,是世界的中心。我說著我對岡仁波齊的全部了解。無數人都會去那朝圣。
她用微妙的眼神看著我,那之中或許有真誠的憐憫,也或許有蔑視,真誠的蔑視。
她說,你連然烏湖都沒看到,想的倒很多。
我啞然地看著遠處的雪山,聽見她興致盎然的聲音傳來。
烏爾朵的比賽這幾年都會舉辦,以前的獎品有瓜果酥油和大米,有酒和鼻煙。她說,你知道嗎?今年的冠軍獎勵三只羊,亞軍兩只,季軍一只。
我感覺自己被什么東西打動了,可我一時不知道那是什么,是三只羊、兩只羊、一只羊,還是女孩平實的聲音。
還真厲害,我問她,你叫什么?她說我的名字好長,外地人記不住的。足有十四個字。我不知哪來的自信告訴她說,我能記得。我想,如果我只認識一個名字有十四個字的人,我一定會記住他的名字。
她被拋在腦后的警戒心這時忽然重新回到她身上了,她后退兩步靠著牦牛,臉上浮現出與剛才談論烏爾朵時全然不同的微笑說,還是不了。我沒有說話,她繼續說,然烏湖很好看,你去看看吧。然后毫不猶豫地揮動長繩,催趕著牦牛離開。
我靜靜地看著她消失在我的視線中。
快要黃昏了,我把倒地的哈雷扶起,推動著走向縣城。我打算找個地方填一填饑腸轆轆的肚子,然后找人修好這輛哈雷。這也許要等到明天才能搞定,至于之后向東還是向西,我還要再想想。 |